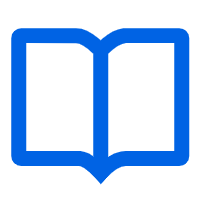只有我不在的街道结局是什么?
只有我不在的街道结局是什么?
在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在东京度过了第一千零一个夜晚。我喝了些日本威士忌,这是我最喜欢的睡前饮料。自从我在四年前的一次企业赞助旅行中结识了威士忌,我便忠实地跟随它,从苏格兰到美国,再到加拿大和日本。所有这些旅行,都是在我的已婚生活之前。我闭着眼喝了一口,咽下时感觉有点刺痛,不过我不介意。人生不是一杯威士忌,你得好好品尝。
我二十六岁时结了婚。我在阿帕拉契山麓的中型报社当记者,那里离首府只有十五分钟的车程。我在那里只工作了两年,但似乎已经呆了好几年。我的工作很闲散,写写花和鸟以及该州的新水族馆,偶尔写写大点的主题,但我不喜欢我的报道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。我嫁给了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人,我们同居了。他的工作和语言都非常出色,而且非常爱干净,或许这有些奇怪,但他也是个酒鬼。我觉得自己知道所有关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故事。我的丈夫,马特,那时是州政府机构中的高级职员,他那强有力的双手扶住了我的臀部,我的身体向前缩,我的脸颊擦过他汗湿的胸膛,在黑暗中的街道中跪倒。在五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,他的气息吹拂着我的脖子。我的丈夫是最优秀的,但我总是觉得他永远不会真正地属于我。
当时我在写回忆录,那是我丈夫去世后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开始的。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,我深深地陷入一场灾难,这场灾难我已经准备好去经历,却也有些措手不及。我从不开车,但那个晚上,也就是四年前的一个寒冷的早春,我偷偷摸摸地,把车开到了高速公路上。我驾驶着一辆福特天霸轿车,那是我丈夫给我买的第一辆新车。我已经知道那场事故的走向。我驾车绕过了一个急转弯,撞到了一座陡峭的山脊上。我的车滑过了高速公路,翻了个底朝天。我昏迷了几个小时,等我醒来的时候,已经身处在一间诊所的诊疗床上,我的头裹着石膏。我无法相信我的眼睛,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。我右臂的骨折处暴露在外,我的X光片显示,许多骨头裂开了,但并没有移位。我甚至不需要手植手术。我带着痛苦和解脱进入了昏迷状态。
当我最终醒来时,我看到了他的脸。一张年轻人的脸,尽管他已经死了。
在洛杉矶的某处,一个二十岁的年轻男子从一家咖啡馆的窗户爬了出来,身上穿着黑西裤和白色衬衫,衣服口袋里装着他所有的东西:几个皱巴巴的纸币,一把梳子,三本平装小说,和一本关于日本鬼的故事的书。一个女服务员发现他之后,把他的东西捡起来,但他从桌上拿起的一本书却从翻开的地方被撕裂了。这是一本平装书,但是很干净,书页平滑如缎,没有痕迹,没有折痕,打开的时候前后页都翻开了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何从窗户跳下。人们叫他“洛杉矶鬼”。报纸把他描述为一个愚蠢的年轻人,为了爱情而选择了死亡。这个年轻人名叫约翰尼斯·埃克曼,我的新家庭医生。
在灾难发生的四年后,我坐着一艘船,航行在威尼斯海湾上。在突尼斯港口,我们迎接了来自美国的旅游团。当导游在讲英语的时候,我听到一个外国人的声音。在人群中仔细看一下,我认出了他。他比我稍大几岁,现在也是已婚了,他的妻子同样美丽,他们有一个孩子。他似乎并不记得我。在突尼斯短暂而艰苦的旅行之后,经过漫长的航程,我们的船在热那亚靠了岸。整个白天我都在哭泣,哭泣声在安静的船舱中回响。当我的丈夫在几个月前第一次试图杀死我的时候,我也曾这样哭泣过。现在我不想再呆在这艘船上,无论它要去哪里。夜晚来临的时候,当所有的欧洲城市都挂上了灯,我离开了酒店,走进夜生活。我回到了意大利南部。我步行了很久,累了,在一座村庄的饭馆中吃了一顿饭,点了酒。我独自饮着葡萄酒,开始聊起天来。隔壁桌有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,我也这样做了。然后我们又跳起身,喝了一些更多的葡萄酒,又喝了一些更为强烈的酒。整个晚上,我们的桌子一直碰撞着,酒杯一再满上。我们相互间大声地说话,很快其他桌子上的人也开始大声地说话。最后,我们大家都站起身,开始跳舞。跳舞,然后继续跳舞,喝干杯,然后喝倒酒,跳啊,跳啊,跳舞。
后来,一个男的把我扶下舞池,送我回到座位上,我哭得泪洒衣襟。我用手背抹去了泪水,拿起我的包,穿过大厅,走到门外。在黑暗中,我靠着一个门柱,深呼吸。我在想,我应该从哪里开始,又是从哪里结束。然后我看到一个穿黑色礼服的男人,向我的方向走来,经过门口时停下脚步,转身看了我片刻。他穿着双排扣的礼服,没打领结,肩上也没任何配饰,只是用手优雅地揽着长裙。然后我看到了他的脸。这太令人意外了,以至于我眨了眨眼,以为刚才看到的一切只是一个梦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相互对视着,他一步步地向我走来。我们相互凝视着,像两艘相撞的船那样靠拢过去。他的微笑仍然未改,不过他的眼神中有些激动。我向他伸出手,他轻柔而狂喜地吻着它。我们紧紧拥抱着,他的双臂将我抱紧,我紧紧地环抱着他。他的双手在运动,我的双手也在颤抖。然后他把我抱上大腿,将我拥入怀中。当我抬头看他时,他笑了。他点了点头,然后再次把我放开。在他的邀请下,我踏入他的汽车,坐在了他身边。他开始说话,但被我的话语打断。
“不”,我说道,“现在该你仔细听我说”。他的左手放在我的大腿上,我感到我的皮肤变粉红,血管中鲜血的流动。他用手抚平我的头发,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后脖颈。我感到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,都在期待他的下一步举动。然后他闭上了眼睛。他突然转向我,开始紧紧地拥抱我。我的双眼紧闭着,脸埋在男人宽阔而结实的胸膛中,听着他的心跳与自己的心跳融合在一起的韵律。他的双手在颤抖,不过他的手臂却十分有力。我在想,他能听见我的呼吸吗?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吗?能感觉到他的心吗?我能感到它正在我的胸口跳动吗?我在想这些并感觉到这些,此时他正在吻我的脖子。
然后他松开我,打开车门,把我送到出租车门口,然后自己也进了另一辆出租车。我回到了酒店房间。我在想他到底是谁。他来自欧洲的某个地方,因为我说英语很奇怪。他是做什么的?我在谷歌上搜他的作品。他的作品很多,十分受欢迎。他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。他的许多书至今仍未被翻译成英文。我打开电脑,开始翻译他的第一本书。它翻译得很糟,因为有些地方无法得到准确的译文,不过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。我已经尽我所能在网上收集与约翰尼斯·埃克曼相关的信息。他的生活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男人,除了他的死亡。他是如何死的,我不清楚。他自杀,或者被谋杀。也许他死了,也许他还活着。或许他就是那个我结婚几周后去世的男人。如果没有的话,我是否爱过他?